《上海戏剧》编者按国家话剧院四台剧目在这个秋季热闹献演后离开上海已有一些时日,然而,关于这次献演、关于这四台戏的思想艺术内涵的议论甚至争论,仍可在坊间时时听到。此处发表的这篇专稿,相信“国话”的艺术家们会有雅量倾听,更期待能有同仁加入这场讨论。毕竟,在当今中国剧坛上,有些直言不讳的批评,总比沉寂或溢美要好得多。文中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国家话剧的文化态度
今年国庆期间,国家话剧院携四台剧目来沪举办“上海话剧周”。说句题外话,这其实该叫“国家话剧周”才对;道理就像意大利电影到上海展映叫“意大利电影展”,而不叫“上海电影展”;中国文化节办到巴黎还是叫“中国文化节”,而不叫“法国文化节”一样。
其时,大幕尚未拉开,紧锣密鼓的媒体攻势就已先声夺人。称“国话”这四台戏台台是“经典”,个个要“震撼”。这使得一向少经典的上海话剧界、一向怕“震撼”的上海“小资”观众像做了亏心事那样先自惭形秽起来。他们一面惶恐地听着京城名导们的训斥:“不知道上海的‘小资话剧’有什么意义”、上海观众要“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话剧”;一面虔诚地从腰包里掏出钱来买票,老老实实地接受“国话”的启蒙教育和四次“心灵震撼”。
上海的某些专家名流(包括名记),按惯例不必自掏腰包,他们的任务是在剧场里鼓掌、会场内捧场、媒体上赞扬。一时间,“精品”、“经典”、“大气”、“窒息”等赞誉之辞漫天乱飞。与之相配合的,是对本地话剧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幸灾乐祸的相互作贱、落井下石的揭短非难。其情其状,好不热闹。由此可见上海人的“海量”。只是上海人的“海量”向来针对外来者,对本地的“异己”却无丝毫的“雅量”,这或许也是“殖民地心态”的一种折射吧。好在艺术作品本身没有封建爵位或行政级别,“国话”又不实行“义务教育”,看它也是要买票的。票子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买了票,自然也有了说三道四的权利。
“国话”文化态度中的两个问题
毋容置疑,由于“国话”丰富的人才资源和严谨的创作态度,这四台戏在演出的完整性、艺术风格的鲜明性和制作的精良等方面,都达到了目前中国话剧的一流水准。然而我认为,“国话”在这次演出活动和演出剧目中所流露或张扬的文化态度,则是落后的。这种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剧目的宣传炒作上,用单一、僵硬的文化价值观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摆出一副“戏剧传教士”和“文化救世主”的面目,令人反感;二是在这些剧目(《恋爱的犀牛》除外)的创作本身,还是高高在上地对观众进行思想灌输、道德说教、审美强迫;以致剧场里充满压抑、累人的气氛。声嘶力竭的叫喊、理性硬块的投掷、声光效果的轰炸……而那些说教大部分不是似是而非,就是无的放矢,甚至还因为严重脱离观众和创作者自身的实际生存状态而显得虚伪和矫情。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尚能信任自己的直觉,尚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就会发现无论是《赵氏孤儿》的悲剧意识,还是《青春禁忌游戏》的善恶之争,或是《萨勒姆的女巫》的灵魂拷问,都无法震撼我们的心灵,而只能“震撼”我们的视听神经。
田版《赵氏孤儿》:一台不唱的中国戏曲、说中国话的外国古剧
田版《赵氏孤儿》似乎是想通过孤儿的命运,并以孤儿的诘问和思索,来重新阐释或者说颠覆这部经典原来的封建“忠”、“义”和“复仇”主题。如果真是这样,那倒是个不错的创意。它也许能使这部古老得难免血腥、陈腐的作品变得更人性化、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也使得这种对经典的解构变得有意义,至少有新意。遗憾的是,目前孤儿在剧中的主线过于孱弱和苍白,创作者除了让其直接向观众诉说外,似乎找不到让他成为戏剧主人公的动作和行动;孤儿“哈姆莱特”式的痛苦和犹豫也缺乏新鲜感。编导还故意摒弃以孤儿的视角展开叙事而将视角分散到每个人物身上,结果既破坏了新的立意的完整统一,又削弱了原来故事的丰富生动,致使整部戏形不成焦点,支离破碎,不知所云。创作者的得意之笔:孤儿最后的沉痛——“原来有两个父亲,现在是一个孤儿”,听起来成了节外生枝。全剧最动人的场面,还是老故事中那些弘扬“忠”、“义”的片断。于是,在客观效果上,对经典的费力解构,成了一次经典对创新的嘲讽。因为整台戏在观众面前张扬的还是在所谓“忠”的名义下的暴行、在大不义的前提下的“义”的灭绝人性。杀气腾腾的舞台上,只有孤儿的生命成了“绝对正义”,而其他的生命价值都成了零。要知道,千百年来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就一直在灌输这样一种信念:在所谓“正义”的旗号下可以无视个人生命存在的价值。只有无知的人才会津津乐道于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为此喝彩?
也许编导的兴趣并不在于内容如何,而是信奉“形式即内容”,只想借经典的素材来完成理想中的话剧形式的重塑。可是,形式即内容是一回事,这种“内容”是否好、是否有价值又是一回事。中国话剧的理想形式,在编导的心中可能有两个参照: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和古希腊悲剧的仪式感。用《赵氏孤儿》这样一部既是传统戏曲又是历史悲剧的作品作为“重塑话剧形式”的素材,似乎最合适不过了。于是编导把在《生死场》等作品里就开始了的实验推向了极端。戏曲中的“唱念做打”,除了唱,全用上了;因为不能唱,便愚蠢地将不文不白、非韵非散的台词以唱的节奏读出,又因为不打字幕(打字幕又太滑稽了),使观众几乎完全不能听懂;而希腊悲剧中的造型的凝重、庄严,叙述的静态、节奏的滞缓,又令人昏昏欲睡,无法忍受。演得累,看得更累。简言之,这是一台不唱的中国戏曲、说中国话的外国古剧。
对这么一次并不成功的实验,编导竟向媒体宣告:这个戏“开创了未来中国话剧的可能”。早已知道某些北京人敢说大话,但这话之大,还是让我吓了一跳。如果那就是“未来的中国话剧”,那么,那种“未来”不来也罢。
莫名其妙的“前苏联”情结
如果说《赵氏孤儿》是在乌托邦似地臆造“未来的中国话剧”,那么《青春禁忌游戏》连同曾经来沪演出过的《这儿的黎明静悄悄》,则是在抒发莫名其妙的“前苏联情结”。我真的不明白,这种在俄罗斯舞台上已经销声匿迹的、连人家自己都抛弃了的东西,我们为何还在那里恋恋不舍?不错,这两个戏似乎都可说是前苏联的“右派戏”,都曾遭受批判。孰不知同一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当矛盾的一方消失了,另一方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君不见当今俄罗斯,有谁还在倾听当年那些遭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了声音,也不需要再有声音。因为他们早就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更何况《青春禁忌游戏》等剧根本谈不上什么“持不同政见”,不过是同一话语情境里的“小骂大帮忙”式的作品而已。
道德从来就不是抽象的,从来就是为维护某种现实利益服务的。“以德治国”,德是工具,治是目的。现实生活中,老婆红杏出墙,丈夫会用道德去谴责她,以维护自己合法的占有权;而一旦他自己有机会和别的女人上床,道德就会被他搁置一旁。这就是道德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同样,《春》剧中女教师为维护既有教育制度乃至社会制度而殉道,令人同情,却谈不上去讴歌。因为那种教育制度乃至社会制度是否值得她去“殉道”,还值得让人怀疑。可是导演却在剧末把她竖成一座纪念碑,并以漫天大雪和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仪式为之祭奠,其倾向性何等鲜明!我真的怀疑这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但愿苏联人民会感激我们。再多说一句,这个戏的编剧技巧甚是老到,其中透露出来的创作观念,我们也倍感“亲切”:“工人阶级的儿子”尽管酗酒、学习成绩差,但本质还是好的,所以被坏蛋打了一拳就转变思想了;而那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一心想研究“颓废阴暗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自私鬼”,却从头到尾一直是卑鄙怯懦的小人。够了,倘想奉行这样的“阶级性”,我们自己就可创作,何必费力“引进”?
品味《青春禁忌游戏》,我不禁联想到前不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同样是取材于教育问题和师生关系的美国当代戏剧《奥利安娜》,两相比较,更觉得前者所表现的文化态度是何其的落后。此处不妨借用孟京辉先生的话:“我对那种戏有仇!”
没有仇的是王晓鹰博士导演的阿瑟·米勒的名剧《萨勒姆的女巫》。尽管晓鹰是我的老朋友,我还是要说,他在阐释这个戏时,对当下的话语情境思考不够,故依然不恰当地采取了一种极其高调、令人生畏的“高台教化”的文化态度。他说,他排这台戏是基于这样一种令他寝食难安的“灵魂拷问”:“面对绞架,我们是选择诚实,还是撒谎?”
如果真想让你的戏引起观众的共鸣或震憾,那就请把调门降低几度
这当真吗,晓鹰?我也许没有理由怀疑你的真诚,不过我想说,这样的“拷问”对当下中国观众而言,是无的放矢,注定落空。也许在基督教国家里,面对基督徒观众,这种“拷问”是有意义的,因为“不撒谎”是基督徒的基本戒律,撒谎是对上帝犯下的一宗罪,是要受到“末日审判”的,这的确是个“严峻的考验”(文革结束不久佐临先生排这出戏时所用的剧名)。而我国的观众不信邪、不信上帝。所以,如果观众事先知道你要这样“拷问”他们,根本用不着你拿出“绞架”,他们立马会给出答案:“撒谎”!所以,晓鹰,你实在是高估了当代中国观众的觉悟。如果你对现实生活有稍稍清醒一些的认识,如果你真想让你的戏引起观众的共鸣或震撼,你就该把调门降低几度,脱下“牧师”的外衣“还俗”。你不妨这样“拷问”观众:“面对金钱、豪宅、美女和官位,我们是选择诚实,还是撒谎?”
当然这仅仅是假设。我知道你不能改写阿瑟·米勒。所以我劝你最好还是放弃对观众进行“拷问”的念头,把戏的重心放在对人性剖析的具体过程中和丰富细节上,这远比虚设一个没有悬念的问题要有趣、深刻得多。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是怎样让人们从不信到疑惑、从疑惑到确信、从确信到加入的,把这一过程放到显微镜下看,隐藏道理,展现现实主义的细节的力量;人物不要类型化,故事不按寓言剧的说法;情节不被逻辑过滤得那么干净,而是貌似生活本身那样自然。如能这样,《萨勒姆的女巫》或许还是会让当下的中国观众自己看出些什么来的,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是“萨勒姆的女巫”,与我们无关。
少拿经典来吓唬人
今天已经不是我们教训观众的年月了,是生活在教训我们和观众。艺术家对于生活和痛苦比一般人敏感和善于表达,那他只需完完全全地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把他所体验到的一切倾诉给观众,以心换心,自然会引起观众的共鸣,不应居高临下地老想着怎么去教训别人、震撼别人。真理是朴素的,真理的形式也应该平易近人。面对戏剧艺术的对话者——观众,如果我们的反应还那么迟钝,态度还那么专横,不理会他们想什么干什么,那他们自然或最终也不会理会我们想什么干什么,那就没我们什么事了。
有人总喜欢拿所谓“经典”来吓唬观众,说穿了是给自己壮胆。似乎一演经典,自己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经典。殊不知,真正的经典创造者都不是靠已经册封为经典的东西成为经典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是如此;焦菊隐、黄佐临也是如此。如果一味经典,将来就没有经典。我们不必迷信经典,经典不过是死人的遗产,艺术的要义存在于活的生命之中。活人不买帐,扛再重的死人来压也没用。何况经典太多,并非都对人胃口。“四书五经”是经典,“三寸金莲”也是经典,更滑稽的还有自相矛盾的所谓“当代经典”。如果只是作为一种促销手段,招徕一班附庸风雅之客,倒也罢了。自己真信,那当就上大了;自己不信,却拿来吓唬别人,堵别人的嘴,就欺人了。
好在上海的话剧人虽然“小家子气”,还不至于自欺欺人。所以,我们宁可“媚俗”,也不要精神压迫;宁可“小资”,也不要没落贵族;宁可观众把看话剧作为“谈恋爱的佐料”,也不要他们连谈恋爱也不看话剧;我们宁可承受一吨的“文化垃圾”,也不要一毫克的“文化毒品”,哪怕它被包装成“精品”,成为“经典”。不若此,“国家话剧”怕只会成为“庙堂话剧”;今天的“主流话剧”怕只会成为将来的“逆流话剧”。而真正的话剧主流、艺术主流将永远只会在受观众爱戴、民间瞩目的泉眼中喷涌而出!
|


 Post By:2008/4/15 11:13:42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4/15 11:13:42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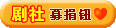 Powered By Dvbbs Version 8.3.0
Powered By Dvbbs Version 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