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3月24日下午2:00—5:30
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东一A201教室
主办:共青团浙江大学委员会
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
承办:浙江大学黑白剧社
主讲:著名先锋戏剧家 牟森
讲座题目:《戏剧态度》
主持人:浙江大学黑白剧社队长 王珂
主持人: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当代著名先锋戏剧家牟森先生来为我们做讲座,机会难得,首先大家对牟森先生的到来表示衷心感谢!(掌声)我们先请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的胡志毅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牟森先生。
胡志毅: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90年代先锋戏剧的创始人牟森先生,进行这次题为“戏剧态度”的讲演。今天在座的有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的研究生,和国际文化学系的本科生,以及浙江大学黑白剧社的同学们。
在90年代戏剧处于低谷的时期,牟森先生导演的《零档案》《彼岸》等等戏剧作品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为中国当代的先锋戏剧开辟了一条道路。明年是中国话剧100周年,我们正在主编《中国话剧艺术通史》,90年代这一章首先就要写到牟森先生。今天能有机会请牟森先生来浙大做客,非常高兴。下面就请牟森先生开始他的讲演。(掌声)
牟森: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同学到场。我刚才和桂老师、胡老师和王珂沟通了一下今天的互动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1,就戏剧态度这个题目表达我单方的理解和感受;2,这次我带来了十多年前演出《彼岸》演出的录像带及《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是十多年前的一个作品,93年北京电影学院演员培训中心十几位同学的结业演出;3,和听众进行交流,回答提问。
* * *
我喜欢米卢,他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态度决定一切。”态度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今天想借戏剧态度这个题目,跟大家讲一讲曾经影响过我的一些戏剧人。
我并非出身专业戏剧院校,而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在座的各位戏剧爱好者一样,我的戏剧实践也是在大学校园里开始的。但是早在我还在校园里的时候,我就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校园戏剧。这个界限很重要。这是一个态度上的区别。
关于校园戏剧,几年前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我曾经说,即使在校园里,戏剧也分为很多种。当然,所有戏剧态度都是共存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没有高下之分。在校园里,逢年过节的文艺晚会,出个节目,自娱自乐,这是一种态度;排演经典作品,请专业演员和导演指导,走专业化的道路,这又是一种态度。还有一种,同学们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编写戏剧,自编自演。在戏剧领域有一句人所共知的话:“一千个导演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我们一千个导演都按照同一种理解排演哈姆雷特,这是一种悲哀。事实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导演对这个角色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诠释。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们排演《哈姆雷特》的时候曾经请我去进行交流,我建议他们排演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版本。如果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做一个法律版的哈姆雷特,有控方、辩方,有证据学的视角,那会是非常有创意的版本。戏剧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我在校园里做的戏剧是区别于联欢会上那一种的。戏剧就是戏剧,不管它是在校园里,还是专业的院团里。
我虽然没有看过大家的戏,但是从桂老师的著作中也对剧社的活动情况略有了解。桂老师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校园戏剧重在参与的过程。” 这是桂老师对于戏剧的一个态度。在浙江大学这样一座综合性的大学里,参加黑白剧社,进行日常训练,排戏、演出,桂老师认为这个参与的过程是最重要的。
这个态度让我想起一个人,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的第一个戏剧人。
1991年我作为美国新闻总署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参观各个学校和剧院时,曾经在华盛顿见到一位名叫罗伯特•亚历山大的老人。这位老人在华盛顿有一个很好的商业剧院,上演的作品都很卖座,此外他又在社区里主持一个生活剧院。这个剧院设在一个人种混杂的社区里,有拉美裔,有非洲裔,有华裔,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参加。第一次见面时我问他的戏剧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戏剧要改变世界。当时我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一个很意识形态化的人,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很左派的一个人。
后来他带我去看他在生活剧院的训练(其中有些训练内容我日后也借鉴过来用在我自己的训练里)。他让每个人进行长时间的身体动作,现场有乐队,在训练过程中他会突然叫停,这时候所有人的身体姿态就会组成某种图景。然后他向在场的每个人提问:“你看到了什么?”当时我觉得自己看到的是名画《沉船》中,一群正在挣扎求生的人。这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
进一步的交流中,亚历山大告诉我,生活剧院的目的并不在于培养演员(尽管剧院里也曾经出过著名演员),而在于,经过这样强度的身体训练,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让每个人都用诗人一样的态度去看待世界。从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健康的角度去面对生活。我后来觉得他确实是在改变世界。这种改变是通过改变每一个个体而完成的。没有比改变人本身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了。亚历山大先生对我的创作时有影响的,我借鉴了他的训练方法,但更重要的是他这种戏剧态度。从我和桂老师的交流中,我感觉到桂老师和黑白剧社给予大家的也是这种收获。每个同学从中得到的东西和改变世界具有相同的性质。改变世界就是改变自我。
* * *
戏剧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文本的历史,一种是演出的历史。在文本的历史中,易卜生和契诃夫是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我自己戏剧实践的血脉来看,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约翰•凯奇。约翰•凯奇是一个不作曲的音乐家,但是他的观念或者说态度影响到了20世纪各个重要的作曲家。大家可能知道4分33秒这个著名的音乐作品,在一个庄重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上,听众们衣冠楚楚地就座,演奏家走上舞台,掀开琴盖,什么也没有演奏,一动不动地坐了4分33秒,然后就合上琴盖,下台。约翰•凯奇认为在这4分33秒中,现场观众因为困惑而发出的窃窃私语、抱怨声、衣裙的磨擦声等等,重叠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音乐。
约翰•凯奇是一位受中国禅宗思想影响很深的音乐家。相遇和发生的随机性是约翰•凯奇最重要的戏剧观念。我有幸在欧洲参观过他的一个展览,从不同的博物馆中各取出一件作品,例如从邮电博物馆里取出一个19世纪的邮箱,从火车博物馆里取出一个站牌,从农业博物馆里取出一个割草机,从戏剧博物馆取出一个灯光机……然后按照概率论的某种算法,在空间中随机地排列这些展品。于是你会在某一个位置上看到火车博物馆的展品和邮电博物馆的展品放在一起,产生了某种含义,换一个角度,而邮电博物馆的东西和农业博物馆的展品放在一起,又是一种新的含义。这次我在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开了一门课,叫“当代艺术的向度、范围、界限和可能性”。在国内戏剧环境里,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和当代艺术有某种血脉关系的人。我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戏剧人,我承认自己受到约翰•凯奇的影响很深。我向他致敬。
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亚洲的戏剧。最初的想法是从演员的个人经历----用我的话叫“个人黑暗的内心深处”----拿出一些属于隐私的经验,来组成演出的文本。但由于和演员沟通时出现问题,最后还是找了一些现成的文本。比如从《等待戈多》中,抽出一部分关于树的台词。当时有一个新闻,日本有一位大学教授远山正英先生,从林业大学退休后,长年组织一批日本的志愿者来中国西北部义务植树。他的报告中有两句话强烈地震撼了我:“第一,中国西北部的荒漠化会影响到日本。第二,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是要到100年以后才会有结果的。”
我把这些和等待戈多中有关树的台词结合到一起。于是这个关于亚洲的主题有了一个等待的意味。在音响部分,我请来了一位叫鹤岗太三的朋友,他是sony音响实验室的工程师,曾经参与东京剧团的工作,以前我们曾经有过合作。这次我告诉他,我要学习约翰凯奇,来一次“相遇”。就是说在排练过程中,所有演员都不知道最终演出时的音乐是什么。,我给鹤岗太三的只有一个90分钟的音乐长度,要求是,用你的音乐独立讲述一个关于亚洲和等待的故事。
经过不断的交流和沟通,最后鹤岗太三确实做到了。在东京首演的那天晚上,开场时的声音是收音机在调频,里面传出一个始终不清晰的女声,时断时续。但当远山正英的形象在舞台上出现,说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要等到一百年以后才会有结果”这段台词的时候,收音机里的声音突然清楚了,是一个女声独唱,歌词的内容是一个女子在二战中等待她的丈夫从战场上归来。其实他已经战死了,但她始终在等待。歌词写得很美,说我等待着你来吻我的嘴,抚摸我的身体,唤醒我的内心。扮演远山正英的老演员当场就被感动了。演出结束后,他走过来拥抱了我一下。
约翰•凯奇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人。虽然他不是一位戏剧家,但他影响到的戏剧工作者远远不止我一个。他的态度和罗伯特•亚历山大又是完全不同的。
* * *
下面我要讲第三个人:皮娜•鲍什,舞蹈剧场的代表人物。她是一位德国的女舞蹈家,开创了一个新的舞蹈种类,叫“舞蹈剧场”,其作品和戏剧的界限已经模糊了。皮娜•鲍什最著名的作品是《穆勒咖啡馆》。她的舞台景象里有很多物体,有时是一排垃圾,有时是满台鲜花,等等。她的舞蹈是人体与物品之间的接触。
皮娜•鲍什有一句名言,可以概括她的戏剧态度:“我不关心人怎么动,我关心什么使人动。”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虽然我的创作还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这种戏剧态度大家可以理解成一种观念,一种哲学,在20世纪的泛戏剧领域里,每个独特的艺术家都能找到这样一句话。理解了这句话,你再看他的作品,就会明白他的作品为什么是这样。
* * *
接下来要说的是大家熟悉的格鲁托夫斯基。这个人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我读大学的时候,戏剧出版社出版过他的名作《迈向质朴戏剧》。中国戏剧导演里有幸看过他的作品录像的不多,我算是其中一个,曾经在一个戏剧博物馆里看过他的《卫城》,一部描写纳粹集中营的作品。我的《零档案》有一年在意大利演出时,他正好在附近的山里做一个工作坊,请我们剧团去那里做客。
格鲁托夫斯基的戏剧观念影响了我很多年的创作实践。这是戏剧领域中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一生都在变,一个创作阶段结束后就很快地转向下一个创作阶段。黄佐临先生最早将格鲁托夫斯基介绍到中国。但是他对贫困戏剧的观念有一点误读。贫困戏剧又译穷困戏剧,就是认为戏剧可以指把布景、灯光等等都去掉,只有两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演员和观众。佐临先生说我们的京剧就是这样。当然他说得没错,但我认为这不是格鲁托夫斯基最根本的戏剧态度。
格鲁托夫斯基早期创作阶段的戏剧态度可以用他书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黑暗的内心深处,藏着我们的痛苦经历,很多童年时期累积下来的东西,有很多篱笆阻碍我们正常、健康地与他人交往。艺术就是让我们内心中黑暗的那部分变得透明,或者说冲破我们内心中那道篱笆的过程。”我认为这是格鲁托夫斯基早期戏剧态度的根本。
格鲁托夫斯基在波兰的剧院叫“十三排剧院”,只有十三排座位,观众非常少。在晚年,他把戏剧归结为“只有演员和观众不能去掉”。他还曾经有一个阶段叫“源头戏剧”,大家知道,戏剧的起源是仪式。格鲁托夫斯基就去世界各地寻找各个不同国家、民族的戏剧起源。在台湾有几位戏剧家,曾经在加州的戏剧节追随过戈鲁托夫斯基,回来后在台湾的山区里做了一系列的戏剧实验。格鲁托夫斯基在晚年发明了一个“节日”的概念。参加训练营的人去旅游,或者去山里过一段时间。他说:“一群无所畏惧的人在一起相处,这就是节日。”这句话让我很震惊。我想,在中国受他影响的不止我一个人。北京师范大学剧社里的一位同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他的研究。
格鲁托夫斯基对演员进行非常严格的身体训练,通过“正身”达到“正心”,通过改变身体来改变心灵。差不多十年以前,我对中国的戏剧学院的训练方法有一些不同看法。在形体训练方面,中戏采用芭蕾的把杆和京剧的一些形体训练。但这些训练都是需要童子功的,而且需要长期持久的训练,才能对身体产生作用。如果不是从童年开始或者不是长期坚持,只能留下一个“范儿”,跟身体内部关系不大。发声训练也一样,美声讲究发声位置,胸腔共鸣等等。但格鲁托夫斯基的训练体系不同。他最基本的系统是建立在瑜伽的基础上的。瑜伽讲究的理念是“我能”。形体上,其动作强调身体内部的变化,只要你做,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作用。格鲁托夫斯基通过这种方式来开掘演员的内心。发声上,格鲁托夫斯基有一个著名观念:“全身都是发声器”。这是和一般戏剧学院的教育理念不同的。
* * *
还有一个人是巴西著名戏剧家奥古斯特波尔。最能代表他戏剧态度的两句话是:第一,“戏剧就是要使人有能力”;第二,“戏剧代表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有一本书就叫《沉默的大多数的戏剧》。他为自己的戏剧观念发展了一整套训练方法。如果说格鲁托夫斯基是出世,奥古斯特波尔则是入世。他希望用戏剧来强烈地介入社会现实,甚至介入政治。中国戏剧家里张广天受他的影响比较大。
* * *
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个性化的、建立在不同个人经历和理想之上的不同的戏剧态度,整个戏剧世界才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一种戏剧态度是远远不够的。回到米卢的那句话,“态度决定一切”。真的是这样。有一位叫魏力新的作者,写过一本访谈录《做戏》,找我写序言,我着重谈的就是戏剧态度。
禅宗有所谓“棒喝”,我就有过这样的体验。有一次我给日本演员排戏,和五个来自不同剧团的演员合作。因为演员在剧团里通常没有自己选择角色的自由,我说如果抛开所有束缚让你们自由选择,你们愿意演什么?有一位长得像个家庭妇女的中年女演员说,我想演布兰奇。布兰奇是《欲望号街车》的女主角。这个角色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和我面前这个演员距离很大,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觉得我和布兰奇一样,是一个有梦想的女人。这句话给我的触动很大,甚至影响到我对戏剧的根本性理解。
戏剧终极所要探讨的是人和人要如何相处。
戏剧态度这个课题太大了,罗列起来恐怕有上百种。我还没有谈到现实主义戏剧,商业戏剧,娱乐戏剧等等,刚才讲到的这些和我早些年的戏剧实践相关。我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成长环境带给我们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带给别人的伤害,伤害是无法避免的,你经常在无意间就伤害了别人。伤害和顽固的自我保护一起,构成了人和人相处的障碍。我刚才谈到的若干位戏剧家和他们在种种戏剧态度支配下的终生的戏剧实践,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想桂老师带给大家的戏剧实践,终极上解决的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问题。包括日常生活的相处,也包括更抽象意义上的相处。
关于戏剧态度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热烈的掌声)


 Post By:2007/3/2 23:52:16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7/3/2 23:52:16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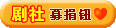 Powered By Dvbbs Version 8.3.0
Powered By Dvbbs Version 8.3.0